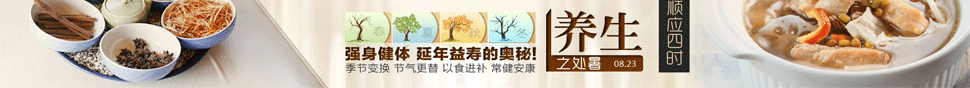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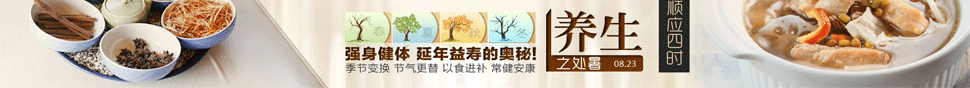
或许,所有的凯撒心中都在疑问,威钦托利何时丢下武器?
前几日北京沙尘,清碧失色,亦是铅华落尽。作为一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人,第一次看见沙尘暴却有着惶然中的麻木,毕竟经历过年,这末日年份似乎像未结清的尾款,还在等待进一步交付,所以拉低的预期永远在告诉你,坏事从来不止一桩,但最终承载付费的又是谁呢?也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世事纷纭卷肃,总不会吝惜个别人的庆幸或脱逃,但窗下的咫尺寸默,或许还是难以揪撇开那隐隐作响的声雷。
坤卦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读《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笔记(个人性复盘,不喜可喷)
一、首先是全球格局的整体迁变,三百年以降,以一、二战及其后的反殖民运动为断代,世界总体的三级格局发生转化——(产业资本时代)帝国资本主义-半殖民半封建-殖民地的整体格局在现代转化为(金融资本时代)核心国-半核心国-边缘国。期间格局转化的主干脉络与因变量体现在以下几点:
a.二战后的欧洲衰败——统治权让渡给美苏——美苏的两极争霸——美国的单极霸权确立。(视为主线)
b.核心国原有的政治及军事强权统治(主要以土地及资源掠夺为主)转变为以强大军事背书、政治意识形态为先导,隐性的金融殖民为根本的统治结构。
c.产业转移及金融自由化:
1、一阶段,二战结束,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比例保证美元的全球通货地位,同时美国战争中累积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商品市场亟待拓展,而美苏的冷战帷幕又随即拉开,由此,带来美国向欧洲的产能输出与大量的主权放贷(马歇尔计划),而苏联也应机拓展地缘战略边界,作出重工业的输出整合,由此,以美苏的地缘争霸边界为界线,大致出现战后的工业化地缘布局
西方(欧洲)——德、法、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
东方(亚洲)——日、韩、台湾/中、朝、印等
2、二阶段,70年代,欧洲及美国产业发展蓬勃,但就此经历内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时发而国内劳资矛盾激烈(由此才有法国“二月风暴”等),同时美国主导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开始绑定石油等大宗期货交易,实现信用货币转变,美元开始出现持续性超发,由此发达各国开始进行传统的制造业产业转移,进行自我经济结构跃迁(金融、环保、高精尖)并缓和国内矛盾。承接此次产业转移的便是具备良好教育基础,人口密度较大,而威权政治为主(可压制内部劳资矛盾,承受低附加值)的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日后便有亚洲四小龙之谓。
而中国在对外开放早期只接收与国内重工业相对互补的产业资本投资,只是在至被西方全面围堵,造成全面经济通缩的困境下才开始转变为对港台资本的引入,以“三来一补”做代工产业,并藉由轻工制造业开启改开后的资本积累过程。
3、三阶段,苏联的自行解体(国内的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黔兵黩武式的过度扩张加之意识形态的侵蚀软化导致自我缴械),敞开出巨大的待货币化的实业资产空间,欧洲对苏俄的战略洗劫被归纳为:a.被金融化;b.金融货币大危机;c.实体资产被超低定价;d.资产被贱价收购。(同步推进的是北约东扩,直指俄国胸腹)。基于这一点,连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全球正式被纳入资本市场的全球体系,获得前所未有的伸展空间。与此同时,欧元开始强势崛起。
4、四阶段,年左右的互联网虚拟经济泡沫,美国开始出现新一轮产业资本外移,新兴经济体开始承接资本输入而表现出经济繁荣,同时,事件后,中国与美国就反恐达成战略协作,美国战略焦点移至中东;经历过98年危机保持汇率稳定并以基础建设投资对冲输入性风险的中国,此时加入WTO,从此开启近15年的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
但中国就此形成与美国的耦合“双输”的循环局面
制造业生产—外贸增长—美元收入—外汇占款——
(国内)货币超发=抑制通胀—流动性进入楼市—地产泡沫(产生三重资本过剩:工业、商业、金融)
(国外)低价商品输出—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元信用保值)—压低美国国内通胀—美联储输出美元—拉高美股—反向收割中国国内优质资产
5、第五阶段,年金融危机,美联储拉低利率,释放巨大流动性进行救市,实体经济苍白,金融资本则变相膨胀,进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造成全球经济动荡,年开始释放结束QE消息,并与英、欧、加、日、瑞签订六方货币互换协议,形成金融核心同盟,由此开始战略调整——美国一则开始大力开发页岩气并寻求资源自给和出口,摆脱中东石油,希图完成自主的美元-资源锚定;其次主导TPP贸易谈判,构建环太平洋贸易圈和“美元湖”,稳定美元的交易货币地位;同时,借助乌克兰危机,挑起欧俄冲突,削弱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在中国周边实施亚太再平衡,意图围堵我国,阻击人民币国际化。
总结两点:
一是,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理论在经济上表现为金融—产业—资源的三元素上下等级,在现代,后面两者受前者主导,并在地缘分布上左右了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历史的国家的命运。核心国家拥有金融主导权和高技术附加值产业,便能在实际的经济博弈中获取超额利润。
二是,这一“核心-边缘”的体系结构的不义在于,一则不事生产的金融资本在天然的超额利润的逐利取向中缺乏有效金融监管,逐渐走向无序。二则其总是核心国家经济危机转嫁的便利工具,可以在对外的寻租过程中,将实际成本转移给边缘国家。三则,这一转嫁直接造成边缘性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动荡,进而引发民生危机,且部分受益国家也承受着巨大的环境透支成本和资源耗竭危机。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共性缺陷:
(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委内瑞拉、南非)
1、除土耳其以外,大部分国家都未经过革命战争获取完整的政治主权,其资源及货币化信用都有所谓的“主权负外部性”,也即在建国过程中基于与原有宗主国谈判作出了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即要么存在大量的土地私人占有或国外跨国公司占有,要不在早期建设资本投入中存在外部性的大量借款。
2、未能形成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工业化半途夭折者多有,由此,一是无法形成良好的民生工业以满足自给,稳定政治结构,二是无法承接产业资本转移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取得制造业产品输出的地位,形成资本积累和良性循环,只能靠外部资本输入形成债务经济,以此对核心金融国产生依附结构。三是,这样的依附结构必然伴随核心金融国的金融涨落而造成经济剧烈波荡,并进一步引发主权旁落。
3、大多数国家欠缺有效的金融管制体系,要么无自觉,要么已被收割而造成体系性失能。
4、单一资源国的资源出口无以为继,会进一步遭致抛弃成为失败国家。
些许感想:
1、主权事大,但同时主权维护除去意志以外,显然需要背后强大的国家能力和足够地缘纵深为依托。
2、家国如人,需要战略定力,在外力的强力拉伸中不能一味的“审时度势”,因为缺乏定力的度势随行只会是机会主义,某些时候的短期受益可能造成的是长期图景的错失与最终的泥足深陷。
3、构建战略,显然是以自主性与良性的能力扩张(循环)为方向的,一时的错误只要未伤及根本的自主能力便是可接受的;那么以此,自主性就是以底限能力的构建为前提的——即如建国以来以政治主权为基石(重工业加持的军事保障)加之民生工业的自给能力(社会矛盾的缓冲前提)——就构成很好的战略回退的空间(纵深)。
4、依旧,政治的根本在于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普世价值下的“友谊政治”既算是人类的理性理想,也难以否弃其巴别塔式的幻象本质,一则既就善良意志而言,地缘文化生长出的语言沟壑昭示的是绝对理解的不可能(既有空间上的隔绝,又有时间上的错位)——求同而存异既表明的努力的方向,但也显明了殊隔的界面。另则,更为根本的,还在于有限资源争夺的大戏让参与方都深切体会着政治的残酷,而猜疑链下的各方都不过是边界的各自试探者。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